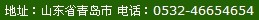|
在理智与情感之外 重新认识我们的肉体本能 向身体的六十万亿细胞 表达迟到的尊重 ” 插画作者:胡晓江 最近几年的短篇写作中,我对肉体本能的暴动有种特别热衷的欢呼。“荷尔蒙”遥遥领先跑在了前头,随后,故事、人物、气氛、见识等,都势利地臣服于这位胜利者,连所谓社会时代因素、批判性逻辑什么的,也被有意抑制、删减与忽略了。我想以这样的方式,对身体的六十万亿细胞表达迟到的尊重与重视。 这些,不见得正确,更谈不上深刻,说局限或也不为过。这是对我自己的诚实:我最近真的就是这么理解和看待世间的。 ——鲁敏 书名:《荷尔蒙夜谈》 作者:鲁敏 出版社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:.01 《荷尔蒙夜谈》是作家鲁敏的最新短篇小说集,收录了其新近创作的十部短篇。作为70后一代的领军作家,鲁敏的写作既讲究传统叙事,又蕴含思辨主题,极富试验精神与现代性,被评论界认为“具有纯正鲜明的艺术信念和训练有素的艺术才能”、“站在中国小说艺术的前沿”。从敦厚乡土的乌托邦书写,到专注解剖暗疾的灰色取景器,鲁敏在这本新书里又一变为冒犯出格的荷尔蒙探索者,以一种“野蛮又天真”的文学姿态,将笔触直指妄动的爱欲俗念,就“荷尔蒙”万有引力般的曲折扩射性影响,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思索与梳理。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,神龙不见首尾的黑社会老大、渴念异性一拥的孤独症少年、谦卑阴鸷的隐秘毒枭、心如槁木亦如铁石的中年妇人、情愿扮演宠物狗的体面官员……人物命运在最原始的本能中起承转合,酷烈与悲凉中成就肉身的大自在。 鲁敏,七十年代生于江苏。十八岁开始工作,历经营业员、企宣、记者、秘书、公务员等职,二十五岁决意写作,欲以小说之虚妄抵抗生活之虚妄。已出版《六人晚餐》《九种忧伤》《取景器》《惹尘埃》《我以虚妄为业》《小流放》《此情无法投递》等作品十八部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读者最喜爱小说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、郁达夫文学奖、中国小说双年奖,入选《人民文学》未来大家TOP20”、“台湾联合文学华文小说界「20under40」等。并有作品译为英、德、法、俄、日、西班牙、阿拉伯等文字。现居南京。 鲁敏 为荷尔蒙背书 在这里讲荷尔蒙,或力比多,或肾上腺素,是为了追求某种貌似科学又带点耸动的效果,其实我所要说的,即是肉体本能。我接连抵押上了好几篇小说、不排除还会继续,以成为其无条件的背书者。 先听我讲几句乏味的来路。在自以为懂得思考的年纪,对构成一个人的几个方面,我曾有个一本正经的排序,降序: 精神。约摸指灵魂,也延及理想、信仰等飘渺之物。/智性。智慧、见识、理智,反正是很有力量的“硬通货”吧。/天赋。才华、异秉、嗜癖等不可追求也无从躲避的东西/情感。大到有立场的家国爱憎,小到花叶飘零的悲欢离散/肉体。既指容貌发肤等可见部分,亦指色声香味触等可感之欲。 看看,肉体是垫底的。倒也不是多么的轻看它,是打小就这么顽固地认为:肉体是可以受苦的、可控制和可践踏的,随便怎样都可以。排在前面的那几样东西,则都是要好好追求、保护和声张的,因为正是它们,在改变、推动并决定着个体命运……那时二十左右,脑子不够用、肉体太刚健,越缺越求,越有的越蔑视。 一年年地过着、在人世中经历,上述这一方阵的排序不断发生着变化,像真是有“所谓人生跑道”那样一个东西似的。 理想主义的大长腿是率先短下去的,虽则心里总也丢拉不下,但哪里经得住混浊现实这索命般的追迫?多情的年纪里,软绵绵的情怀与烈焰燃炽的理性之光常有局部博弈,要么心中一动要么心中一硬。有一个阶段,则跟在众人后头一个劲儿地嚷,信仰啊信仰,一切问题都出在信仰上!或又有那么几年,沉浸在世俗生活中,乃至产生一种崇拜的、五体投地般的虚心,认定这生活本身便有着至高无上的教义……反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,不同阶段之中,一会儿来这出,一会儿是那出,诸种要素轮流坐庄,但再怎么变幻,“肉体”是从来没有跑到最前面去领头的,因为总觉得:道理上讲不通。 讲不通大概也就对了。因肉体与它的几位“跑友”不同,它一直是,不讲道理的。 人丛中一瞥的心脏骤停,皮肤摩擦时的视线涣散,梦境的投射,胃的痉挛、细胞们的脱落,各种边缘性非理性的衍生物最终构成了我们的身体,这个复杂、可笑又亲切的东西,与人生的一切大道理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对峙。这悲壮又偶杂喜剧性的过程中,我总会眼睁睁地看到,学问啦情谊啦天赋啦,常会在具体的情境中遭遇困难,气喘吁吁地相互妨碍、纷自沦落,最终恰恰倒是它,肉体(或曰荷尔蒙、力比多,如前所说),以一种野蛮到近乎天真的姿态,笔直地撞向红线,拿下最终的赛局—— 浊世中一幕又一幕悲喜,云图中一场又一场胜败,如果放大滚滚长河中的那些慢动作,分解、切割开来看,总会发现肌肉、骨骼、血液与器官的强大意志、独立意志。饥饿与刺冷,会跟歇斯底里的情欲一样,具有黑沉沉的杀伤力。一声轻佻的耳语,半头疲惫的白发,会使一个人出门向左,而非向右,并微妙影响到他所在的局部世界,其起伏、明暗、质量和关键性走向……看看吧,这漫长的跑道上,肉皮囊虽不是最高级,但绝对小看不得,甚或可以高看。所有那些大人物、小人物,男人物,女人物,实质都是以肉身为介质,为渡桥,为隘口,从个体走向他人,从群族走向代际,最终构成了世相与历史…… 以上交待的仅是个人想法。而这些缺乏条理的想法,总会像摇荡着的风景一样,折映到小说这片小水塘里去。我以前写《铁血信鸽》《谢伯茂之死》,是对智性特别着迷的阶段。写《取景器》《墙上的父亲》,无疑,情感上的投射是强烈的。而最近写的这些小东西,则对肉体本能的暴动有种特别热衷的欢呼。《三人二足》《坠落美学》《万有引力》《徐记鸭往事》都是这样的,“荷尔蒙”它遥遥领先跑在了前头,随后,故事、人物、气氛、见识等,都势利地臣服于这位胜利者,就连所谓批判性逻辑、社会时代因素什么的,也被有意抑制、删减与忽略了。我很想以这样的方式,对身体的60万亿细胞表达迟到的尊重与重视。 这些,不见得正确,更谈不上深刻,说局限或也差不离。这只是事实,我最近真的就是这么理解和看待世间的。 内容选读 大宴(上)杨早今天有大变化,连老爹都注意到了。蠕动着中风者的僵硬舌头,老人家吐出半句听不清的质问。杨早冷酷不语,伺候好老爹拉完晨屎、吃完早饭,随即出门了。 他在马路上架着肩膀急促地走,四肢好像加长了,显得僵硬。快到姐姐家时,在巷子口先后遇到两个面熟之人:钱某与肖某。当年姐姐闹离婚时,这两人曾经出过力气跑过腿脚,杨早也仅仅是很小幅度地收了收下巴,没有一丝笑意。杨早从不这样的。从前看到熟人,他总是老远就做起笑的准备,趋前搓手,孤儿式的笑容,孱弱、机灵,并伴有适量的感恩。他注意到钱某颇为惊骇的样子,肖某则拼命揉眼睛。也不管了。 杨早拍杨宛的门,很响。口袋里就有钥匙,他常来照顾两岁的小外甥豆豆。 杨宛隔着门细声询问,听出是弟弟,语气更慌了:“你钥匙呢?出事了?”她拉开门,恐惧地直打量弟弟,好像他丢了一只胳膊。姐姐越来越像母亲了。老娘在世时也是这样,外面随便刮个小风,她即会为之焦心,担心家里根本就没有晒出去的被子。 杨早简单地命令杨宛坐下,刚要张口,杨宛指指帘子后面,“嘘”了一声:“直咳到天蒙蒙亮,才睡着。这百日咳啊,还真是要一百日。”姐姐开始讲豆豆,医院、挂过几次水、花了几多钱什么的。声音空洞不知所云,带着怕事者的有意拖延。 杨早低下头听着她讲。杨宛讲了一串,挨不下去了:“到底出什么事了?你这样子……” “得着个,机会,可以,请容哥,吃饭。”怕吓着姐姐,杨早特意讲得很慢。这个消息,他已经憋了一整夜了,跟小豆豆一样,他也是天蒙蒙亮才睡着。 “容哥?”杨宛赶紧笑,笑得呆滞和犹豫。 这难道还要解释?她当真从没听说过容哥?杨早鼻孔张大。一、二、三。他在心里默默地数。如果三秒钟内她能反应过来,还可以原谅。 “哦,容哥,是容哥啊。”杨宛移开眼睛,心虚得直点头。他妈的。杨早只得凑近她解释。杨宛听了一遍,又混浊地重复一遍,随即满面警惕:“现在还有这个?”她有种小姑娘似的愚昧:世界就是她所看到的那个样子,就是新闻上所看到的那个样子。 “当然有了!越发达的地方越是有,你想想外国!再想想现在我们多像外国!”杨早耐着性子解释。他给姐姐大致讲了一下《教父》,又讲了一部韩国片子《新世界》,以帮助姐姐理解容哥的背景及其地位。杨宛嘴巴半张,听得十分认真,听完了,却一扭头,窸窸窣窣地做起卫生。这间层高不足两米五的单室套,虽则背光,虽则只有屁股大小,也算是姐姐最大的固定资产,极度的珍爱使得她竭力追求纤尘不染。她跪下来擦地,口气里的抱怨接近幸福:“亏好死畜生拿走了那套大房子,否则搞卫生我也吃不消的。”“死畜生”是她对前夫的专用称谓。“死畜生”一直不按时给豆豆抚养费,杨早去讨要过几次,去一次给打一次,那死畜生身高一米八二。 看着杨宛勉力而侥幸般的抹地动作,杨早越发感到疲惫。这个家,算上老爹和豆豆,尽是老弱病残妇幼,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个投奔处,连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。他闭上眼睛,把头搁到硬邦邦的椅背上,那隐约的孤儿感又来了。他真怀念小时候,爸妈都是大人,姐姐也是大人,他只管安心地做着小孩子,啥也不懂啥也不烦。现在不行了,除非他出头,否则这个家就像死光了一样的。可他哪里出得了头,他自己也是个货嘛。杨早曾经翻过几页《曾国藩家书》,盗版的,别字连篇,不影响看的,看到曾国藩把家里大小事体、子弟前程安排得那样妥当,杨早真是羡慕死了,哪怕能投奔了去做他的家仆也好——这几乎就是他最大的志向了。想到这里,杨早突然冒出一个联想,这容哥,可不就相当于他所向往的曾国藩吗?也许更好呢!据说,在那一行里,对老弱病残妇幼是最为照顾的,这是他们的一个伟大传统…… 这样想着,杨早又稍振作些了。即便没有人商量,也要做成这件事。就由着姐姐这么糊涂着吧,她真要问三问四,也难讲的。 消息源自一个不便透露的渠道,用朋友的话讲,是“绝对可靠”的,最核心的部分是,大约半月之后,有个饭局会请到容哥出场,在开泰酒家,目前还空出一两个席位,朋友说他可以介绍杨早去坐那个空出的位子——听到的第一秒钟,杨早就感到他的耳朵给死命地拎起来了,拎得他整个人都离地了——这可不是去夹几筷子菜、喝两三盅酒,那等于是傻到地狱了。跟容哥同席的机会这辈子只会有这一回,他必须把它做到最大,做到改变命运的程度。 他结巴着,胆怯似的向朋友表示了感激之情,心里面却冷静得像一块生铁。他瞬间拿下一个硬主意:他要去埋单,替这顿饭埋单,由他来请容哥吃饭! 请黑老大吃饭。杨早被这句话的含义及能量给震慑了。什么概念啊,脚下简直就像铺了一条笔直的大红毯子啊——首先,容哥会对他有一个初步的印象。然后,他会趁着热和劲儿去涎着脸,去踮起脚,去舔屁股,去反复跑动、反复靠近,被冷淡一万次、拒绝一万次也绝不放弃。杨早认为自己是做得出的,也是必须去做的。只要最终能让容哥“认领”下他,那就万事大吉,等于有势力和后台了。到那时候,就把家里的大事小事好好捋捋,按照轻重缓急排顺序,但第一个得先搞定那个“死畜生”,再不拿出抚养费的话就让容哥派人卸他一条腿,真的,一条大腿!绝不含糊。 帘子后的豆豆翻了个身,猛咳起来,杨宛仓促地放下抹布,湿淋淋地正堆在杨早的脚面上,她满嘴“小乖乖醒了,小乖乖醒了”地冲到床边。杨早踢开抹布,走上前亲一下小外甥打算告辞。梦中乍醒的婴孩,本能地回亲着他,信赖地把两只肉乎乎的小手环上他的脖子。杨宛用儿语在一边念着旁白:“哎哟,小舅舅来看我们了,舅舅一来宝宝就不咳了!就要全好了!”这样的瞬间,单调又凄凉,好像与这小婴孩的一生、他未来的光明或坠落,有着严密的关系。杨早一阵心悸。 没说的,得请容哥吃饭。 次日晚上,杨早十一点半下班,发现杨宛等在家里,脸上的神情跟他昨天早晨去找她时相似:有话。可杨早无力应付了。他开的是40路车,40路是一条彻头彻尾的破烂路线,一头是城郊接合部,有几个假装说着要拆迁的化工厂,另一头是小商品批发市场。上来的乘客要么大包小包,不外乎是拖鞋、头花、胸罩、太阳帽之类,总共不值几个钱,散发出低等货特有的坏塑料味儿;要么是一本正经打算进城消费的人,被汗水渍透的深色套装,衣领上带着崭新的折痕。他们三三两两高声谈论各自的事情,所有的核心,归结起来,其实就一个:钞票。听得杨早越发烦躁。只有末班车会空荡下来,路灯光和月光交替,照着黏糊糊满是脚印的车厢地面。相貌平常的女乘客默然坐在最后一排。杨早有时会想象,他将来的女朋友,最好就在这个时候上来,坐他的车,来接他下班。杨早在等红灯时,尝试念叨:女朋友。还真他妈拗口。 杨宛给他带了一饭盒的饺子,十八个,她弄什么东西都喜欢个吉利数字,或是借以掩饰分量上的不足。老爹胃口大开,一下子吃掉十一个,用半边腮帮子贪婪地嚼,衣领和被头上落了一层油乎乎的馅儿。不能怪老人家嘴馋,杨宛上一次有心情包饺子,还是她离婚前的事。 余下的七个,杨早端到厨房去吃。他吃得挺快,杨宛说得更快,每个饺子她能说出十几句话来。她终于晓得容哥是谁了。她转过弯了,似乎又转得太猛,冒出一大串冰糖葫芦般的想法。比如,她也要去吃晚饭,豆豆也要去,最好还带上老爹。另外,要准备礼物,有分量的大礼。还有,晚饭后如果容哥要“消遣”的话,杨早也要出面全部包下来。总之,抓住这一下子,要干得绝对漂亮,让容哥印象深刻。 “消遣?”这不是杨宛可以想到的词。杨早胃里猛地一抽,还是咽下了最后一个饺子,他昨天忘了交代一句:请容哥的事,绝对要保密。当时看杨宛那神气,以为她不会往心里去。 “是老钱提醒我的,肖姐也想到的。哪有吃完晚饭就散的,要再玩乐玩乐的。他们同意共同分担晚饭后面的花费——我跟他们提的要求。”杨宛龇着牙,小心地流露出一点得意,她不太习惯这个表情,随即又恢复了一贯的惶然,“定在哪家酒店?我想去打听一下价格,有个数。” 杨早拿筷子直敲空盘子,像唱曲儿的——气愤的曲儿:“还豆豆,还老爹,还老钱,还肖姐。你把容哥的饭局当成菜市场了!让我跟朋友怎么交代?人家可把我当个自己人!” 杨宛声音变尖,这是她要哭的前兆:“是他们两个先跑到我家的,说你肯定有好事。我随口说出容哥,他们简直就要冲我跪下来。这个要怪你自己,好好的路上碰到,为什么不跟人家打招呼。再说,老钱和肖姐当初为我离婚,一个跟死畜生打过架,一个帮我抢下豆豆。你嘛,打又打不过,抢又不敢抢。” 杨早不敲盘子了。杨宛开始收拾桌子,手上有活,声音又慢慢稳定了:“他们也打了包票,凡事先来后到,等你跟容哥的关系稳了,咱们家的闹心事都搞定了,再轮到他们。你也晓得的,老钱是想要吃个低保,肖姐是儿子想考公务员。谁不想走容哥的路子啊。” “低保!公务员!你以为容哥是市长啊。”杨早又想敲盘子,桌子上已经空了。看看吧,人还能蠢到这种地步。他这一天下来所受的累都比不上这几分钟的。 “市长算什么,跟容哥不能比的。老钱、肖姐他们跟我讲了半天容哥的事,中午还请我吃了一碗牛肉粉丝汤,然后下午接着讲。这么说吧,从生下来到幼儿园到考大学到出国,到找工作、找老婆、找警察、找医生,直到找墓地,你这一辈子可能会碰到的所有难处……”杨宛停了一下,显然惊诧于自己的语速,“就跟你昨天讲的电影一样。但凡摆不平的,容哥全都可以。” 七个饺子堵在胸口,永远也消化不了似的,“可是,那里只有一两个空位子。” 杨宛微微一笑,显然老钱和肖姐早跟她讨论过:“可以加座的,实在不行,还可以换大桌子。人多更有排场,容哥能不喜欢?反正咱们请客嘛。”她那口气,好像很清楚容哥的脾气。杨宛在超市做收银,这工作带给她一个结结实实的逻辑:多就是好,越多越好。 杨早没精打采地脱下外套,准备刷牙。事已至此,他真说不动了。杨宛期期艾艾地一直跟到卫生间:“我带上豆豆,是想替他认个干爷爷。你想,要有这层关系那多硬实……容哥多大年纪?认干爹还是干爷爷?” “你忘了,豆豆一见生人就要哭的。”杨早拼命往嘴里捅牙刷。刷牙的时候,整个脑袋晃动,听不到杨宛说什么。他只是注意到杨宛的脸突然红扑扑的,她倚在门口,把头发放下来,摆到胸前然后又甩到脑后,她挤在杨早边上,对着小半片镜子扭腰送胯。 杨早吐漱口水,听清杨宛的后半句:“……这么收拾一下,还可以的吧。听你的,我不带豆豆了。就当我是单身。” “唔?”杨早差点儿咽下泡沫。她疯了呀。 “我听他们讲容哥那些事,估猜着,他并不喜欢年纪很轻的女人。”杨宛飞快地补充了一句,不理会杨早像是要把漱口水吐到她脸上的样子。 房间里老爹在拍床,也许已拍了好一会儿。杨宛殷勤地跑过去,一到门口,就扭头出来了:“好好,全听你的,那天也不带老爹。”杨早跨进老爹卧室,韭菜与鸡蛋的呕吐物气味,像暮春的热风一样,迎面而来。老爹方才饺子吃猛了。 接下来几天,为了商议请客一事,杨早杨宛走动频繁。老钱和肖姐起初是间接地通过杨宛参与讨论、发表意见。但传话的过程太辛苦,又易出错。杨早的气也慢慢消了。不久,他们两个便堂皇地加入进来,变成了四人小组。 肖姐会准备一点鸭四件,老钱会拎上半打啤酒,杨宛则油炸一盘花生米。每次都会吃光喝光,要商量的事情实在很多。比如大家如何自我介绍并替对方介绍、各人的角色定位、当天的着装、见面礼的选择等等。在反复的设计与推翻之后,大家一致同意,要确保杨早作为重点人物,他的亮相和印象是最要紧的,别的人,可退而求其次。关于见面礼,分歧非常之大,仅为这个,连续争论过三个晚上。老钱认为一定要高雅,比如字画古玩,肖姐觉得实惠更好,最新款手机怎么样?但到了第四天,杨宛无意中抱怨了一句什么,他们瞬间神奇地达成了共识:不送了!什么也不送!理由是怕显得太露骨。其实呢,杨早心里清楚,其他三位也同样清楚,就跟他每天开40路车所听到的那些车轱辘话一样,原因只一个:钞票。 费时最多的讨论放在埋单一事上。这是整个宴请的重点,也是杨早这个四人小组的成败所系——在什么节点埋?以什么方式埋?既不能埋得过分隐蔽,更不能轻佻、了不起似的。最好能显得幽默、忠诚,让容哥知会到,并印象深刻……这真的非常之难。几番讨论,都拿不出能共同通过的方案。每到进行不下去的时候,大家就换一个话题。 比如,换到“消遣”一事,气氛会生动得多。谁来过渡与引导?如何捕捉出容哥的趣味?打牌、打球,还是打炮?大家相互间已经越来越信任了,老钱和杨早就着话头交换了关于“小姐”的经验,他们说得挺深入的,轻蔑又内行。肖姐在一边直摇头,故意等了一会儿才打断:“容哥哪会稀罕这个?他与她们,应当算是一个系统的吧。”老钱正谈在兴头上,不高兴地愣住,随即也哂笑了:“倒也是呢。何止是这个?其实所有的行业都跟他是一个系统的,这世界上估计都没有他稀罕的东西!” 喝啤酒吃花生米的时候,他们就完全地吹牛、瞎侃,借以纡解紧张的神经。肖姐喜欢谈论有权有势者,那些亮光闪闪、大进大出的事情。老钱则爱讲烧抢掳掠、祸害劫难,恐吓而生动的语气。杨宛最没出息,医院、丢钱包、接到诈骗电话之类的细碎烦恼,听得大家都颇为不耐烦。但这些不同方向的话题,交叉进行着,最终会像麻花辫一样,拧成同一股力量、汇成同一个信念——等结识容哥之后,一切好的事情,我们也会有份儿了,而一切不好的,自有容哥去替我们摆平。这一愉快的寄托像一段没头没脑但不断增强的旋律,萦绕在他们四个人头脑的上方。夜晚的灯光下,他们的影子互相交叠,富有生机、气势不凡。 商谈的战线拉得太长了,也过分谨慎,效率越来越低,但杨早的心情反倒慢慢好了起来。他现在很庆幸有老钱和肖姐的参与,他的不安由此被平摊到一整个团队了。肖姐虽是女流之辈,比姐姐还大几岁,但她几乎全天开着半导体,掌握许多冷僻但有用的信息。老钱的脑筋弯弯绕,具有一种粗犷的马路智慧,多少能撑着杨早。 到临近宴请日的那一阵子,他们更是每晚一见,哪怕杨早当天是大夜班,也会从公交公司直接赶来参加。考虑到一帘之隔还在百日咳的豆豆,大家更加地压低声音,有时讲着讲着,其中有一个人都快要睡着了。只要有人推推他或她,提到容哥二字,这人就像被抽了一鞭子似的,抽搐一下,带着甜美的弹性回转过来。是的,容哥!他们马上就要请容哥吃饭了。他妈的,哪怕就只是想想看吧,还要睡吗? 这过程中,杨早忽略杨宛了。有天众人散去,他口焦得厉害,再要杯水喝,蒙眬得睁不开的睡眼中,忽然注意到杨宛脑袋有变。顶上一把稀稀的头发,既烫又染,成了褐中带红的满头卷。左腮上原来两粒小肉痣,不见了。眉毛显然也动过。最触目的是她的牙齿,雪白,日光灯下简直瘆人。 “你干吗?”杨早困得犯恶心,努力集中精神。 “看你喝水啊。”杨宛好像比以前有态度了,以前她不会这样讲话的。她眼光放空、若有所思地,“……双语幼儿园、双语小学,说不定我家豆豆中学就能到美国去了,就怕到时我舍不得。”她顿一顿,眼光拉回来,像为了显示觉悟,“你放心,先搞定老爹,让容哥找个头等专家,把病给弄好。” 见杨早仍然在瞪眼,她明白了,扭扭脖子,简单地说明:“连肖姐都在减肥,她都四十二岁了。再说我是真正单身呢。” “你和肖姐也不想想,人家容哥……”杨早水喝急了,胃里一阵晃荡。 “没多想,只是顺便想一想。这个怎么样?”杨宛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只缀满假水晶的公主发夹,小心地撑到额头上,调整了几下,使得水晶花居于额头四分之三的位置。她现在有两处在发亮了:水晶花和牙齿。她练习着夜生活的那种笑:“这样引人注目吧?” “索性抱上豆豆得了,那更引人注目。”杨早讽刺道。 “会带豆豆的。”杨宛语调平静,爱护地取下发夹,“他们两个都要另外带人。我们不带的话就吃亏了。”他们还要另外带人!杨早使劲撑开眼,极度的瞌睡突然变作了剧烈的头痛。杨宛声音变得远了,“你带谁呢?真的没女朋友?我可提醒你,这是个绝好的机会,带个女孩来,让她看看你的本事……”杨早扭头就跑,飞快跑下楼,好像他听不到这些话,就不会发生似的。 夜色荒凉,参差不齐的黝黑树影更加深了他的噩梦感。头痛得恨不能剁下来扔到路边,可这病痛却也使他获得了某种自弃的权利,他麻木地拖着腿往家里走——随便吧,一切随便好了。 长按右侧QQ营销工资2000白癫风那家三甲好
|
当前位置: 百日咳_百日咳 >荷尔蒙夜谈鲁敏出格之作,向衣冠楚
荷尔蒙夜谈鲁敏出格之作,向衣冠楚
时间:2018-8-26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健康秋季干咳怎么办试试这几种食疗
- 下一篇文章: 宝宝哮喘怎么办防喘牢记这几招4